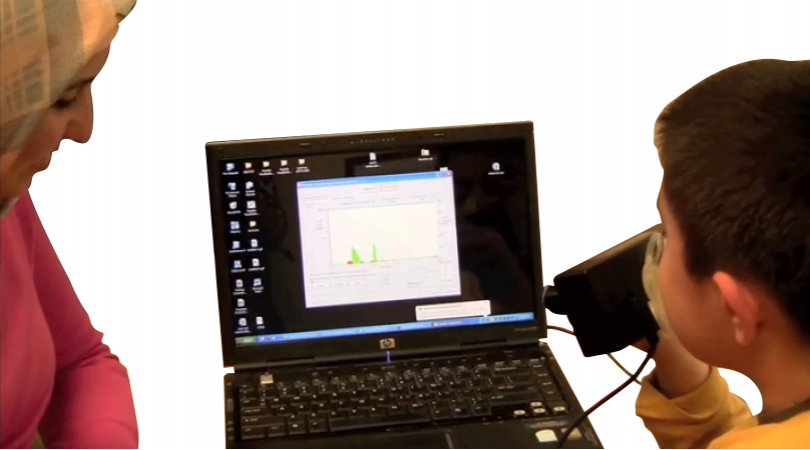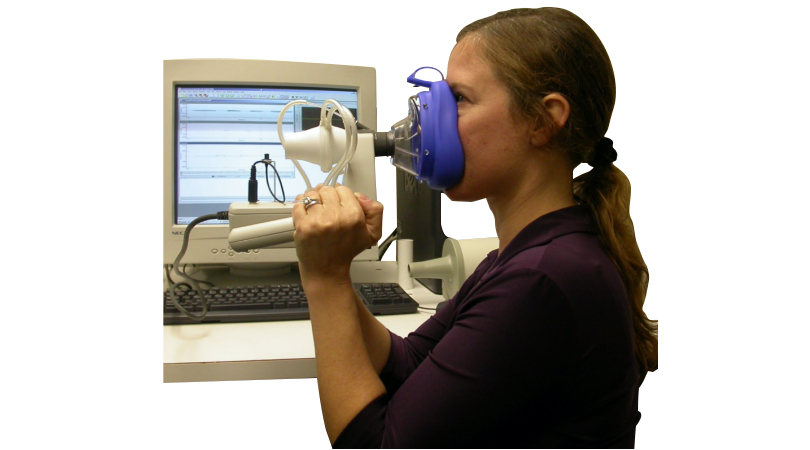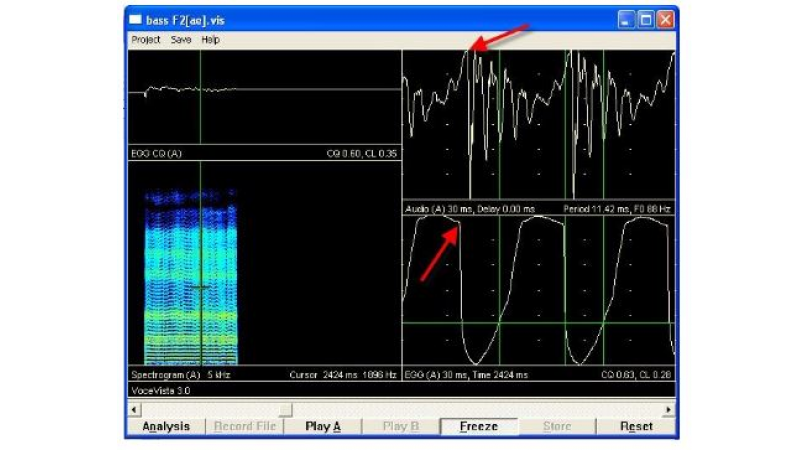3504 阅读 2021-05-31 10:31:12 上传
以下文章来源于 文献语言学
甲骨文“南”及相关字补说
黄博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
摘要: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对甲骨文“南”字的构形理据与本义作了进一步探索。本文认为甲骨文“南”字当是“醓”的本字,本义为肉酱;“南”字形象有盖“筒形器”,盖子上覆有植物;甲骨卜辞常见的贞人名“

”字形象手持勺类器物挹取肉酱,也应读为“南”;据甲骨文“南”字的特殊写法,本文还尝试对西周金文读为“总”的疑难字形提出自己的意见。
关键词:甲骨文 考释 南 醓
一、甲骨文“南”字形体分析
甲骨文中“南”字习见,写法主要有如下几种:
A:






(A类字形分别见于:《合集》20415[1]、《合集》20627、《合集》378正、《合集》10903、《合集》32036、《合集》36975)
B:






(B类字形分别见于:《合集》20536、《合集》20537+、《合集》12870乙、《合集》8742、《英藏》0754、《合集》28192)
C:









(C类字形分别见于:《合集》2030、《合集》24429 、《合集》32606、《合集》33178、《合集》30374、《合集》32242、《合集》24939、《合集》28320、《屯南》2360)
D:



(D类字形分别见于:《合集》15620+、《乙编》4511、《合集》15654)
E:





(E类字形分别见于:《合集》33241、《合集》33241、《合集》33246+、《合集》34220、《屯南》1270)
F:



(F类字形分别见于:《花东》14、《花东》38、《花东》270)
A组字形最为常见,上部作“

”形,下部作“

”形;[2]B组字形在“

”形上多加一横笔,当是无意义的“饰笔”,“同”在作偏旁时,中间也有写成三横笔的情况,如甲骨文“興”字:



(以上字形分别见于:《合集》19907、《合集》16081、《合集》31066)
C组字形在A、B两组的基础上,于“

”形中间再加一短横笔或短竖笔;D组字形把C组字形“

”形中的短横笔或短竖笔变成了空心块状;E组字形仅见于历类卜辞,与其他组类差异较大,属于“南”字的一种简体,[3]上部省作“

”形,下部所从“

”形两侧笔画均向外弯曲。陈剑先生指出,历类卜辞用字存在不规范性,体现在历类卜辞中保存体现文字原始性的用字现象比较多,[4]“南”字似又可为此提供一个例子。F组仅见于花东卜辞,其特点是“

”形上部的“

”形左右两笔不对称,应是植物的象形。另外,五组形体所从的“

”都与“

”形紧连在一起。除《合集》36975“

”外,[5]“

”形下部几乎不出头,均作“

”形。
宾类卜辞屡见的贞人名“

”,其字形从“南”从“

”,学者或权宜地写成“殻”“㱿”等,其名已见于商代记名金文:
G:






(G类字形分别见于:《合集》734正、《合集》3614、《合集》6887、《集成》2971、《集成》6782、《集成》9161)
H:



(H类字形分别见于:《合集》32正、《合集》171正、《合集》7061臼)
“

”的主要写法有以上两种,G组字形显然是“南”作偏旁时的简省写法,由于“

”字经常出现,刻手为求简便,将“

”形下部的“

”与“同”形两侧连成一笔刻出。需要注意的是,“

”字所从“

”形上部往往靠近“南”旁上部的“

”形而不是下方的“

”形。
二、以往研究的简要评述
“南”字在卜辞主要中有三种用法,除用作方位名词和祖先名“南庚”之“南”外,“南”字还表示一种祭物的名称,以往的学者多有论及,主要观点有两种:一是“乐器”说,认为甲骨文的“南”字是表示的是钟镈一类的乐器,“

”字像手持槌击打乐器“南”;二是“畜子之通称”说,把祭物之“南”释为“

”,读为“豰”,解释为“畜子之通称”,将“

”释为“㱿”,贞人“

”也因此被称为“殻”。此外,还有学者认为甲骨文“南”字本象商代的头盔之形。[6]
白于蓝先生对卜辞中祭物之“南”也作了细致的研究(下简称白文)[7],白文不同意上述两种观点,在梳理了上述两种观点的形成过程后,着重指明了“畜子之通称”说的缺陷。不过,白文最终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观点。
第一种观点由郭沫若最早提出,他说:
由字之形象而言(按:即“南”字),余以为殆钟镈之类之乐器,……字作

、

乃象一手持槌以击南,与磬、鼓二字同意。殸作

、

诸形,鼓作

若

即象持槌以击鼓,知

与磬、鼓必系同类字,又

即磬形,

即鼓形,则知

南同字,而南与磬、鼓亦必为同类。……以声类求之,当即古之铃字。[8]
白文认为此说“虽有一定的字形依据,但由于郭氏在论述的过程中以古文字中‘南’与‘㐭’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字强加附会,读作‘铃’亦与卜辞即典籍中通常所见之祭物名称不符”,白文的批评是中肯的。不过,郭氏据“磬”、“鼓”二字形体认识到“南”、“

”同字的意见值得重视。
近年来仍有学者信从“乐器说”。季旭升先生认为:“甲骨文南字,象乐器之形,……字下部象器体,上部象悬挂的绳子”,[9]前面已经提到,“

”字的“

”旁上部往往靠近“南”旁上部的“

”形,若“

”字表示“持搥击南”,为何“

”要击打悬挂“南”的绳子呢?况且“

”字所从“

”旁与磬、鼓所从的“

”旁表示的并不是一物(详后文)。卜辞中祭物之“南”往往与“牛”、“羊”等牲畜并举,把“南”解释为“乐器”也无法读通相关卜辞,“乐器说”在字形和辞例上都有无法弥补的缺陷,亦未被多数学者相信,连郭氏本人最后也放弃了该说。
第二种观点以唐兰为代表,郭沫若加以补充。白文从形音义上指出了这种观点的缺陷:从字形上看,用作祭物的“南”与方位名词之“南”、“南庚”之“南”别无二致,单把用作祭物的“南”释为“

”,自相矛盾;从读音上看,“南”与“

”声韵皆不近,没有通假的可能;从用例上看也存在诸多障碍,特别是卜辞中的“新南”不好解释。白文的反驳有理有据,令人信服。接着白文又分别梳理了古文字中“

”字与“南”字的形体演变脉络,认为“南”与“

”是来源不同的两个字,贞人“

”自然也不能读为“殻”。白文的一大贡献在于成功区分了古文字中的“南”字与“

”字,使得二者之间再无瓜葛,纠正了学界长期以来对“南”、“

”的不当认识,白文功不可没。白文最后对“祭物”之“南”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读法:一是读为“腩”,指干肉或肉羹;二是读为“醓”,即《说文》之“

”“䏙”,指肉汁或肉酱,至于哪一种是祭物之“南”的本义,白文认为“目前尚难论定”。
总之,目前学界对卜辞中祭物之“南”缺少统一、明确的认识,还有重新讨论的必要。
三、祭物之“南”所在辞例分析
白文的另一贡献在于对卜辞中用作“祭物”之“南”字的分析。我们遵循白文的思路,先来分析祭物之“南”在卜辞中的用例。白文罗列有关卜辞,总结出祭物之“南”在卜辞中常与犬、羊、豕、豖、牛、牢同为祭物,“南”字前后均可加数量值,且主要使用“燎”“卯”“

”“㞢”四种祭祀方法:[10]
甲申卜,贞:翌乙酉㞢于祖乙牢㞢一牛,㞢南。
《合集》25+《合集》2551+《合集》15165+《合集》18003[11]
贞:御妇好于父乙,衁牢㞢南,

十牢、十、南十。
《合集》702正
来庚寅衁一牛匕庚,

十、十牢、十南。
《合集》893正
乙巳卜,宾贞:㞢于祖乙二南。
《合集》1528
庚戌卜,争贞:燎于西,

一犬、一南,燎四豕、四羊、南二,卯十牛、南一。
《英藏》1250
燎于东、西,㞢伐,卯南、黄牛。
《合集》14315+《合集》1076+《乙补》4875[12]
燎五牢,卯三南。
《合集》12954+《合集》15620[13]
卜辞中出现了“新南”一词:
贞:九羌,卯九牛、新南。
《合集》360
贞:

妣庚新南。
《合集》724
贞:祼于父乙新南㞢羊。
《合集》2219正
贞:㞢于父乙白彖、[14]新南。
《英藏》79
贞:燎于王亥五牛、新南。
《英藏》1175
白文发现,卜辞中祭物名称之“南”与当香酒讲之“鬯”字用法接近,白文的依据主要有三:一是“鬯”前也可出现“燎”“卯”“

”“㞢”祭祀方式;二是卜辞中有“新南”的一词,也屡见“新鬯”一词;三是卜辞“

”字仅在“南”“鬯”两种祭物前使用过,在其他祭物之前未见使用。
先看第一点。“鬯”前出现“燎”“卯”“

”“㞢”的卜辞,白文列举如下(释文有改动):
丙午卜,宾贞:燎鬯。
贞:燎鬯㞢豕。
贞:勿

燎鬯。
《合集》1506
来庚寅,

衁三羊于妣庚……

伐廿、鬯卅、牢卅、三

。
《合集》22229
甲寅卜贞:三卜用,血三羊,

伐廿、鬯卅、牢卅、三

,于妣庚。
《合集》22231
丁丑卜,贞:王宾武丁,伐十人、卯二牢、鬯□卣,亡尤。
庚辰卜,贞:王宾且庚。伐二人,卯二牢,鬯□卣。亡尤。
丁酉卜,贞:王宾文武丁。伐三十人,卯六牢,鬯六卣。亡尤。
《合集》35355
丙申卜,即贞:父丁岁又鬯。
《合集》23227
癸未卜,宗岁又鬯。
《合集》30336
“燎”“卯”“

”“㞢”在祭祀卜辞中使用频繁,需逐个分析。“燎”字,《说文》解释为“柴祭天也”,“燎牲畜”、“燎南”、“燎鬯”常出现在祭祀卜辞,说明牲畜、南、鬯可以被“燎”,推测“燎”的目的可能是使牲畜、鬯等食物的香气更加浓郁,达到祭祀祖先的目的,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:“卬盛于豆,于豆于登,其香始升,上帝居歆。”郑玄笺:“其馨香始上行,上帝则安而歆飨之”,祖先飨用的即祭品馨香的气嗅。白文认为“卯”字也可以在“鬯”前出现,其实是一种误解。“卯”可以出现在“鬯”字之前,但却不能与“鬯”连用。上举《合集》35355,“卯”的对象是“牢”不是“鬯”,卜辞中也未见到“卯鬯”或“卯几鬯”的说法,“卯”的对象往往是“牛”、“羊”或“牢”,学者多理解为剖牲法,[15] “南”是可以被“卯”的,前文所举卜辞已经提到,这恰恰是“南”与“鬯”的不同之处。“

”字常用于祭祀卜辞或军事卜辞敌对方国之前,于省吾认为“

”字并非册告之义。“

”以“册”为音符,应读为“删”,俗作“砍”。[16]但据前举《合集》35355 ,“鬯”也可以被“

”,这似乎对于说不利,其实,把“

”解释为“册告”也并非无据,在祭祀卜辞中,“

”字后会出现不同种类的祭物,往往还要说出祭物的数量,如前举《合集》702正、893正、22229、22231,“

”很可能是一种仪式:在祭祀前向祖先“册告”祭品的内容。
卜辞中屡见“新鬯”,出现的次数要比“新南”多:
辛酉卜,王其登新鬯…
《合集》30974+《合集》31720[17]
癸丑卜,子祼新鬯于祖甲,用。
《花东》248
卜辞中只有“南”、“鬯”两物前出现了“

”字:
㞢于祖辛

南。
《合集》655正甲
贞:

南于父乙。
《合集》2263正
贞:

鬯于祖乙。
《合补》84[18]

鬯于祖辛
贞:王入。
勿

鬯。
《合集》10584+《合补》6113[19]
陈剑先生认为甲骨金文中的“

”字“作以刀向豕之形,表‘剥皮’‘割裂’等之义至为明显”;[20]蒋玉斌先生认为,“

”字可能对应《诗经》中的“剥”字,《诗经·小雅·信南山》:“是剥是菹,献之皇祖。”郑笺:“剥削淹渍以为菹”。总之,“

”应是同时适用于“南”、“鬯”的一种动作。
我们发现,“南”和“鬯”前还都出现了“祼”字:
贞:祼于父乙新南㞢羊。
《合集》2219正
甲午卜,贞:今日夕祼南。
《合集》15835
丙辰卜,贞:祼告㕦*疾于丁新鬯。
《合集》13740
壬午卜,

贞:于丁祼鬯,于之若。
《合集》24132
“南”和“鬯”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,二者均是可以被用于祭祀的食物。此外,“南”可以被“祼”,说明“南”可能也是流状类的食物。“鬯”是浸以郁草的香酒,因其味道馨香,遂成为供祖先飨用的祭物。所以,不如干脆把“南”理解成一种味道鲜香的流状食物。
下面来说说“南”和“鬯”的不同之处。除了前面提到的“南”可以被“卯”而“鬯”不能被“卯”外,我们发现,虽然“南”与“鬯”都有“数词+南”、“南+数词”和“数词+鬯”“鬯+数词”的用例,但“鬯”字后可接单位“卣”,如:
祖丁燎鬯三卣。
《合集》27301
“鬯+数词+卣”的用例多见,上举《合集》35355也能说明。奇怪的是,“南+数词+单位”的用例我们却没有见到,并且“南+数词”的用例明显比“数词+南”的用例多,联系甲骨文“南”字的形体,推测“南”可能是本身带有单位的食物。
以往学者把“南”读为“豰”,解释为“畜子之通称”,依据之一是卜辞中食物之“南”常与“牛”“羊”“牢”等物并列出现,但仔细品味“南”字出现的卜辞,会发现“南”常列在“牛”“羊”“牢”等祭物的后面,在同一条卜辞中,“南”的数量基本不会超过“牛”“羊”“牢”的数量:
贞:□年于王亥,

犬一、羊一、豖一,燎三小牢、卯九牛、三南、三羌。
《合集》378正
翌庚辰燎十豖南二。
《合集》1385+《乙补》5934+《乙补》3126[21]
□□卜,争贞:燎

百羊、百牛、百豕、南五十。
《英藏》1256
“南”很像是“牛”“羊”“牢”等祭物经过处理加工后的食物。
(未完待续……)
注释
[1] 对于所引片号有缀合者,一般将缀合诸片全部引出,并加注说明缀合出处;若所引甲骨片号仅是列举,则在片号后缀以“+”,表示此版有缀合。
[2]“

”即“同”字, 详参王子杨:《甲骨文旧释“凡”之字绝大多数当释为“同”——兼谈“同”、“凡”之别》,《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》,上海:中西书局,2013年,第198—230页。
[3] 连劭名先生已注意到此类“南”字写法与其他组类有别,参连劭名:《甲骨文字考释》,转引自于省吾主编,姚孝遂按语编纂:《甲骨文字诂林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6年,第2871页。
[4] 陈剑:《殷墟卜辞的分期分类对甲骨文字考释的重要性》,《甲骨金文考释论集》,北京:线装书局,2007年,第439—448页。
[5] 《合集》36975从“木”从“

”,从辞例上看确是“南”字,与“桐”字形似。甲骨文“桐”字作“

”(《乙编》9067)、“

”(《屯南》2152)等形,“南”字上部大多从“

”,“

”下部不出头且与“

”形相连,笔画相交,“桐”字从“木”且上下部分不相交,王子杨先生已有论述,详参王子杨:《甲骨文旧释“凡”之字绝大多数当释为“同”——兼谈“同”、“凡”之别》,《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》,第218页注。
[6] 连佳鹏:《释“

”》,《汉字文化》2010年第3期。
[7] 白于蓝:《说甲骨卜辞中“南”字的一种特殊用法》,《中国文字》新32期,台北:艺文印书馆,2006年,第57-62页;收入《拾遗录——出土文献研究》,北京:科学出版社,2017年,第1-16页。
[8] 郭沫若:《甲骨文字研究·释南》,参于省吾主编,姚孝遂按语编纂:《甲骨文字诂林》第2862-2864页。
[9] 季旭升:《说文新证》,台北:艺文印书馆,2014年,第505页。
[10] 释文采用宽式,尽量使用通用字。有些姑作权宜隶定的字,在右上角加*标记。
[11] 《合集》25+15165+18003为蒋玉斌先生缀合,见蒋玉斌:《蒋玉斌甲骨缀合总表》第176组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,2011年3月20日,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2305.html,李爱辉先生加缀《合集》2551,见李爱辉:《甲骨拼合第250则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,2014年1月21日,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3620.html;收入《甲骨拼合四集》,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16年,第168—169页。
[12] 林宏明:《甲骨新缀第394例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,2012年12月6日,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2861.html。
[13] 蒋玉斌:《甲骨新缀第1—12组》第2组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,2011年3月20日,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2306.html。
[14] 从陈剑先生释,参陈剑:《金文“彖”字考释》,《甲骨金文考释论集》,第243—272页。
[15] 于省吾主编,姚孝遂按语编纂:《甲骨文字诂林》,第3438页。
[16] 于省吾:《甲骨文字释林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9年,第194—196页。
[17] 林宏明:《醉古集——甲骨的缀合与研究》,台北:万卷楼,2011年,第152—153页。
[18] 即《合集》5808+《合集》1298,蔡哲茂先生缀合,见《甲骨缀合集》,台北:乐学书局,1999年,第235—236页。
[19] 蔡哲茂:《〈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藏甲骨文字〉新缀第六则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,2008年8月21日,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1755.html。
[20] 陈剑:《金文“彖”字考释》,《甲骨金文考释论集》第266页。
[21] 林宏明:《甲骨新缀第830—834例》第八三一例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,2018年12月28日,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11319.html。
本文原载《出土文献》2020年第4期,引用请据原文。由于原文篇幅较长,故分为上、下两篇刊发。